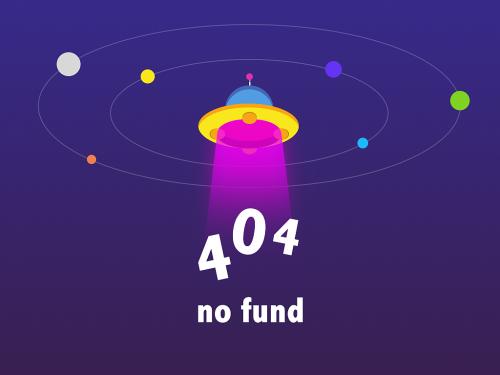就在今年,外公外婆因拆迁搬进了城里,我知道,我彻底告别了那座小乡村。
那是个冬日里总是被阳光眷顾的小乡村。亮晶晶的阳光,在老人手织的毛线帽上跳跃,给洗得泛白的围裙也着上了色彩。阳光映照下,老人们容光焕发,甚至都年轻了几十岁。光阴,总是格外偏袒这片桃花源。
我的童年是这幅乡村山水画的一隅,背景是青黛色的山,珊瑚色的落日,金黄的麦浪,还有戴着草帽辛勤劳作的外婆,而我只负责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奔跑,用脚丫亲吻沉默温柔的大地。我和伙伴们一起追逐黄色的蝴蝶,捞河中的小螺蛳,寻找路边的野草莓,对于这片土地,我们永远不会疲倦,永远不会觉得腻。偶尔,它也会有新奇的狗血鸡毛,会有闹腾的婚丧嫁娶,这便成了妇人的乐趣。
每当我躺在高高的谷垛上面,站在流淌的大河边,坐在古老的石头上,萌生的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憧憬,更多的是对这里的爱意。这里的孩子想的从来不是逃离,而是在出去见过很多大山大河后,仍能回到这片土地。
再次回乡,已是年后,当年豆蔻年华的小女孩已成为风华正茂的大学生,可是只有破败的青石屋打不起精神地等着我,黑漆漆的,空寂寂的,在阳光下昏昏欲睡。年轻一代早已带着孩子进城,只留下年岁已高的老人,而老人又多半逝世,随意葬在田间。放眼望去,像土丘般凸起的就是简易的坟墓。
这里安静得可怕,绕过萧索破败的茅草屋和野蛮生长的杂草,面前的田地荒着,脚下的碎瓦片多得出奇,大多是拆掉的石屋的瓦片。只有落寞的阳光照着更落寞的老人,而老人,望着一步步走远的初阳,目光里溢满了悲伤。那只小卖部门前的黑狗,如今瘦得只剩骨头,也只会冲着我叫,把我当陌生人。禁不住回想起当年的阳光,当年的毛线帽、围裙,和当年老人亮晶晶的眼眸……
村里没有了孩子的笑声,记忆中的槐树、枣树不在,曾经槐花飘香,醺醉了整座村庄,陪我摇花树的伙伴不在;曾经枣子熟透,甜到了人们心间,和我用竹竿击打枝条抢甜枣的“敌人们”也不在。他们早已带着老人的不舍,为了所谓的前途和远方,离开了这座村庄。
记忆中那么多嘘寒问暖的人不见了,都去哪了?下庄没有人了,下庄快要消失了。南边不过百米就是高速公路,不在这里停歇的汽车呼啸而过,沿途是被荒芜杂草取代的麦田,风一吹,记忆中的金色麦浪不复存在,只裹挟着呛人的尘土。我向远处望,前方是拔地而起的高楼,是嚣张入侵的城市,而我的背后,是低矮破旧的石屋,是手无寸铁的故乡。
人们总以为00后桀骜不驯,不可一世,喜新厌旧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代名词,其实身处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,我们未尝没有自己的怀旧和悲哀。
终于,乡村的每个人成功从土地拔根,移植到精致的水泥房,努力把自己同化成城里人,羞于谈起自己的小村庄。《汉书》曾说:“富贵不归故乡,如衣锦夜行”,在那个时代,回乡做官,是无上光荣的事。但在这个时代,乡,还是衣锦荣归的去处吗?若他日有幸衣锦,我该去哪里还乡?
去外地上大学后,我仍然能从屋脊城墙上,清楚地看到远山的乡愁天际线,和郑雷孙先生一样,挂在那条乡愁的天际线上,努力摇曳也只是徒劳的思念。我们这群异乡者,最终的归宿又在哪里呢?
我思念着一座已经消失的村庄。
我留不住记忆里的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