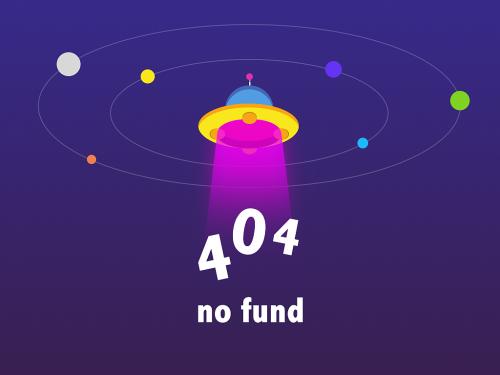我从小就讨厌喝粥。我不喜欢粥黏糊糊的口感,不喜欢粥里干苦的百合和莲子,不喜欢黑米的口感和豆子的腥味。还有枣皮卡在上牙膛,枣核剌嘴的糟糕感觉。但我们家每天都要做“黑豆八宝粥”,放了所有我讨厌吃的“营养食物”进去。每天家里都要逼我喝粥,所以我一直期待着哪天可以喝到放了菜和肉的异类粥。
我还没等到家里往粥里放肉,先得到了部队裁军的消息,爸爸在名单上。
我不知道爸爸的心情如何,只知道那天的妈妈非常愤怒。她没有做粥,那天晚上只有番茄炒蛋和土豆丝,都是我爱吃但妈妈不给做的菜,我很开心。但是爸爸不在餐桌上,我又有些失落。
过了几天,爸爸跟他的雷达和机器告别,也和他的军旅生涯正式告别。过两年我就要上初中,海淀的学区房价格已经有了膨胀的兆头,他不知道以后该去做什么。家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粥,桌子上常常是长茎青菜、蘑菇和蒸土豆。妈妈经常把苹果当成晚饭。我的牙从小就是烂的,那些青菜连嚼都嚼不动。
在那之后的某个晚上,我把半根青菜吞进了气管。青菜又长又韧,我吐着舌头说不出话,盯着妈妈哭,妈妈不知道该做什么,便跟着我一起哭。她哭得眼睛都睁不开,看起来比我更厉害,脸憋得分外地红。我把手伸进嘴里去扯那根青菜,顶着强烈的异物感和撕裂感取出了它。那是极其长的一根油菜。妈妈掩面哭得更厉害了。
“妈妈,妈妈我想喝粥。”我哭着说。
“好,好,给你做。”她一抽一抽地说。我们家的粥回归了,食谱上的油菜被永远地划去。妈妈开始喜欢做加了南瓜的白粥,她很少会放那些味道多变的薏米和黑豆。但是南瓜太糯还带丝,还有古怪的根块味,我依旧不喜欢喝。
那个时候爸爸在准备考公务员,晚上常常不同我和妈妈一起吃饭,更不如说妈妈不让他上桌吃饭。晚上送我进屋后,隔着门总能听到他们大声说话。我听着他们的声音睡不着,仰头看着窗外大货车驶过的余光,如同指针一般拨过,轰隆隆的声音走远,便是开过了一辆。车灯的余光里会有精灵,我坚信着精灵哪一天一定会帮我带走粥里的南瓜。
又过了一段时间,那些暗红色、暗绿色的公务员考试书被收了起来。爸爸开始迷茫地枯坐,他的头发白了一圈,我们家的粥里也有很久没见过黑豆了。南瓜也没有了,变成了单纯的白粥或者小米粥。这样的粥里虽然没有肉和菜,但是有谷物的清香和微甜,我很喜欢喝。如果把炒过的冬瓜或者白菜拌进去就更好喝了。
家里喝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单纯的粥。晚上的声音没有了,放假的时候能看到白天枯坐的爸爸,晚上枯坐的妈妈。他们一致地倚在椅背上,把身体全部的重量放在上面。爸爸在沙发上收拾了个床位,没几周沙发被睡坏了,便拿透明胶带把它填补继续睡。
沙发变成胶带沙发一段时间后,家里多了张陌生的折叠桌子,买了巨大的冰箱,两口很大的不锈钢蒸锅。那样大的冰箱和锅我只在饭店里见过。爸爸好像在暗中忙活着什么。那几天的晚上总能听到妈妈提起“姑姑”“两万”这样的字眼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,他们找同样过得不是很好的姑姑借了几万块钱,很久都没有还。
一个早上,我突然喝到了皮蛋瘦肉粥。
极白的浓稠大米,被细心切碎的皮蛋还有肉花融化在两手才能捧起来的塑料杯子里。粥装得极满,灰白的液体顺着杯壁溢出来,黏在手上,舔一舔是甜的。喝一口先是极浓郁的猪油香味,大米的软糯香甜包裹了皮蛋的腥涩和肉花的鲜咸,即便如此也没能掩盖谷物的清香。还有一点黑胡椒粉锦上添花作为最末的刺激。
太好喝了,我从未喝到过那样好喝的粥。把塑料杯内壁上的最后一点舔干净,回头一看,那折叠桌上整齐码着无数杯一模一样的粥。我问爸爸自己还能不能再喝一杯。
“不能再喝了哦,爸爸要去出摊。”爸爸笑了,不做军人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笑。
但他过了几个小时就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手里没有剩下的粥,我很失望。那天之后我再没见过铁皮折叠桌。晚上,门外一男一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他们这次声音格外大,我听到城管和巡警没收了爸爸所有的“作案工具”。那段时间查得很严,要不是爸爸身体素质有底子跑得快,就要被罚款了。因为从小十分正义的家教,我没有为爸爸感到悲伤。
爸爸的借钱创业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巨大的冰箱,但这次失败的经历多少启发了他。他从我同学的爸爸那里了解到警察编制,经过电话的确认,他发现自己作为转业军人是可以被分配至警察局的。说来有点的讽刺,爸爸转业的方向,也是巡警。
爸爸很快办了手续,接受了筛选和培训。他很幸运地成了中心城区之一——朝阳区的巡警。那个时候的朝阳警察并没有现在这样出名,三里屯的也没被曝出那么多新闻。警察虽然没有假期,但是福利待遇和工资都是以前的翻倍。
黑豆黑米又出现在了粥里,裂皮的大枣被升级成了润滑的小枣。除了百合和莲子,粥里还多出了银耳和枸杞。粥底里还放了些小米和红糖进去,偶尔还会有薏米和葡萄干。黑米软糯,豆香厚重,小枣甜软。百合微苦的清脆叶片被红糖制服,取了莲心的莲子也不再难以下咽。银耳增添了顺滑的口感,葡萄干点缀了口中的惊艳。
“黑豆八宝粥”变甜了,也好喝了很多。